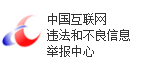疯狂的租房业
常住人口只有五万人的贺兰县城长宽不过几里地,却或许是中国租房业务最繁忙的小城市。这个秘密张扬在它大街小巷的信息张贴栏,栏上的房屋出租转让的广告纸层层叠叠,一条广告的寿命常常捱不过2个钟头,就会有急等着变现和加入这座城市的人撕走。
如果将广告上的小区剪贴,会发现拼成的地图几乎就是整座城市。贺兰县城居身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界,空旷处向西远眺可以看到贺兰山高大黑黢的身形,而往北就是腾格里沙漠。展开于黄河冲积扇上的街道平直宽阔,房屋整齐地排列在街道的两边。新建的小区在城市周边扩散开来,由于多数房屋建于最近几年,小城给人簇新之感。泥头车和塔吊密布城市的边缘,仍推动着小城在地面的扩张和高度上的跨越。
这是一座不停开价售卖的城池。填补空缺的人群低调神秘,他们通过信息栏同这个城市取得联系,拨通那些广告上留下的电话号码,缴纳租金然后填充那些闲置空间,给房屋带去温度,为窗户打上灯光。对于这些人的身份,知情人总显得难以启齿。
王飞雷是贺兰县工商局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负责全县违规经济活动的纠察,从2009年开始他与同事们就开始了与神秘人群的周旋,并陷入日后他们疲于应付的“猫鼠游戏”。“鼠”是指需要隐藏的一方,是潜伏于县城庞大的传销网络。“最高峰时期,这里聚集的传销人员有近20000人。”这令他和同事们感到头疼,在这个常住人口不多的城市里,每四个人中就可能有一人是传销分子。
“贺兰是南派传销在西北最深入的据点。”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曾于2009年底前往贺兰县解救参与传销人员,当时正处在贺兰县传销组织的发展时期。此后,他所领导的反传销组织又多次派志愿者前往贺兰进行解救活动。一个内陆腹地的小县城聚集了这么大量传销人员,在他经验中绝无仅有。
在城市如同海绵一样膨胀开来的同时,传销分子也像吃水一样浸了进去。传销人员的加入,使得原本宁静的小城被撕裂成两个平行世界。面色黝黑的本地人,每天晨练、上班、吃羊肉饭、睡觉,按照社会管理和秩序过着平淡普通的日子。与此同时,另一群人则受控于庞大的传销组织,他们多数来自河南、江西、四川等地,没有正式职业,大部分时间待在出租房里,三五一群“串门”学习传销知识,被一个暴富神话鼓噪得难以入睡。
因为传销组织的严厉规范,两者之间并无太多接触,只是空间上刚好都在一座小城里。大部分贺兰人对于租住他们房屋的人了解仅限于“外地人”,房租一年一交都通过银行转账,至于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则说不清楚。这种隔阂,使得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两者在小城中相安无事,达成某种平衡,这里是一个有着二元世界的地方,界限井然。
并无交集的两个世界却有一个重合点,这是贺兰县城中心的欣兰广场。欣兰广场是当地人饭后休憩的地方,也是传销组织和成员心中的“圣地”
网络图 | 贺兰县城
圣地
作为本地人,宋美云从欣兰广场建立开始便在这里工作,她是广场的管理人员。常年的观察,她发觉来广场休憩的本地人多数都是一家子,晒晒太阳、散散步,等寒冬炎夏时人就不多了。而操着外地口音的游览者则是寒暑不辍,他们多数穿戴整齐,有着不同于本地人的白皙面容,三五一群,指来指去,像领导考察一样。
虽然占据着打量这座城市的最佳“观测点”,宋美云并不知道她所管理的欣兰广场是传销组织的洗脑基地,被尊称为“行业的宝塔山”。这座2002年建成的广场位于小城中央,占地8万平方米,气势恢宏。
“他们很规矩,有生人就不说话,只听说这些人是搞传销的哩。”她看到,这些“考察的人”一般会从广场东边进入,经过一座钟楼,然后在一棵樟树下停留几分钟,之后走上喷泉台,之后从广场西缘出去。让她惶惑的是,被这些人奉为神树膜拜的居然是一棵死樟树。这棵移植的樟树前两年死了,只留下枯枝干部分,每个树杈都分成两个枝桠。为了不影响美观,工作人员用一些塑料花草对这棵树进行了装饰,并用装饰布将树干裹了起来。
图 | 这颗枯死了的樟树,被传销组织视为圣树
郭宇是王飞雷的同事,通过长期与传销人员的交手他才弄明白欣兰广场一草一木在传销课程中对应的解释。广场东边的大钟,是“持久牌”钟表厂生产,寓意“行业持久”。而“树杈分作两枝”则代表贺兰传销行业“一个人可以带两个人”发展,树干缠裹着装饰布条是暗示“行业有国家支持”。
“广场液晶显示屏背后有5台空调机降温,被称为“五级”;喷泉台有3级阶梯,则意味着“三阶”;合起来就是传销行业的模式‘五级三阶制’。”这个被“神格化”的广场一切都被赋予同传销有关的意义,将传销行业所有的知识点形象化,并且不断为行业新的谎言提供佐证。
宋美云关于“神树为何是死树”的疑惑很快就被传销组织攻克。“树死了,就意味着‘一个人带两个人’这是个死规定,不能破例。”
被忽悠进传销组织的人们,一遍遍地来到这个广场,瞻仰每一处“神迹”,将他们第一次在这里听过的“神话”,讲给之后带来的人听。平时只能潜伏在县城出租屋里的“梦想者”,在这里进行着他们唯一露天的“精神生活”,同当地人站在了一起沐浴阳光和风,不过彼此无关。虽然荒谬不经,但这些神话故事确有其吸引力,不然难以解释在欣兰广场“考察”的人群几乎从未断过。
“他们说广场喷泉有600个喷头,被解释为够600份的参与者就可以躺着拿钱。”作为一个打击传销的执法人员,郭宇知道,他所见到的每一个传销者都曾无数次来过这个广场。“但却没有一个人识破,那个喷泉的喷头明明是800个。”
市民休闲地、行业教学基地、洗脑的教堂,比之小城的撕裂,欣兰广场似乎更甚一层,作为实实在在的实物,却又是一个虚空谎言的生产地。
网络图 | 赵作海曾在贺兰传销组织被骗数万元
打而不绝
传销势力进入贺兰的时间已不可考证,但流传下来的故事却颇具宗教色彩。贺兰传销组织内口耳相传,数年前为了扶植西部大开发的进行,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24名“行业精英”在一个深夜被一辆军车从广西北海秘密护送到宁夏。“资本运作”事业由此在当地扎下根来,并开枝散叶。
“实际上,南派传销正是从广西扩散到云贵川,再到甘肃、宁夏的。”对全国传销状况了如指掌的李旭觉得,上述传说是有其真实脚本的。广西是南派传销的发源地,北海、南宁、来宾等地都曾十分猖獗,近年来南派传销逐渐北移,沿途城市纷纷沦陷。南派传销脱离了北派传销“以实物销售作为基础,控制人身自由”的窠臼,而仅以缴纳现金作为入行条件,更为隐秘也难以被侦查到。
传销分子选中贺兰县城绝非偶然,王飞雷发现传销组织最感兴趣的就是贺兰充足的房屋资源。贺兰县城离银川仅10公里,被称作银川的“后花园”,房价却只有银川的一半,空气和绿化都较好。近年来贺兰县城新开的楼盘就有七十余个,在这些楼盘中,占地3000亩的太阳城小区号称可居住50000人,这差不多能住下县城所有的常住人口。
“贺兰县城房价低且闲置率高,而且房屋建设都很漂亮,和在其他地方相比,这里简直是天堂。”郭宇说,传销分子最常见就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城乡接合部,过着大锅饭、集体住宿的苦日子。小城作为一个内地县城的城市管理比大城市则显得较为宽松,降低了传销行业存在的风险。传销分子在这里找到了“世外桃源”。
贺兰当地政府对传销的打击,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力度最大的时候,当时传销组织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包下了大巴车从太阳城直接发往河南,号称逃出贺兰县就是胜利。”郭宇说,2011年夏天那次专项整治后,有不少传销组织为了保存下来,整体迁往中卫、固原等地。小城震动,政府新闻网站扬眉吐气地写道:火车票代售点门口买票的人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龙,其中80%的人买去往河南的火车票。
根据2011年6月16日至8月1日的统计,贺兰县打传人员共入户走访6653户,发现涉嫌传销窝点679个,发现涉嫌传销人员1927人。在打击行动中,郭宇和他的同事们每敲开十户房门,就有一户是传销窝点。
图 | 当地一直在打击非法传销
药渣
几年折腾下来,拥有最佳观察位置的宋美云已经掌握了这个小城的“脉动”。
她发现欣兰广场“考察”人群的疏密度与县城房价、租金和菜价都存在着正相关的联系,人多时房价涨菜价高,人少时房价就下跌。而碰到严打传销的时节,租金菜价就一起往下掉。作为城市化的受益者,她家的土地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被征收,获得三套房子的补偿,如今家人住一套房,另外两套就被用于出租。
2011年6月时,是贺兰传销最为猖獗的时候,欣兰广场的人络绎不绝,宋美云家的房子租出了最高的价一年一万多元,她的邻居甚至租上了一万五。贺兰很多小区的房价也一路涨破五千。虽然心里开心,但菜市场的菜价却都上涨了,原先两三元一斤的蒜薹,却卖到了7元钱,比过年还贵。而等之后全县清查传销,她家的房子租金又一路降到了三四千元。
网络图 | 当地在疏散传销人员
鸡和鱼是“体系”内特别敬奉的食物,取其谐音“机遇”。体系内有一位山西的酒厂老板,负责造起了“鸡鱼酒”。每月1号,是行业内的“机遇日”,这天大家都要吃“鸡鱼宴”。在传销旺季,鸡鱼的销量,会明显影响整个贺兰县的菜市场。
“为了保存下来,组织内制定了严格生活管理方案,禁止与当地人来往,细节方面也是严抓严防。”来自周口的刘生财平时就在太阳城小区门口卖水果,和他一样小区里所有的摊贩几乎都是“组织”的成员,只是分属不同的“山头”而已。很多人甚至把孩子都带到了这里,就在小区里的学校上学。
有成功者,也有落魄者。而刘生财是一个从“初级业务员”奋斗到“高级业务员”再落魄为小贩的典型。他自己的70万陷进去,背后还有一大批被自己引进来的亲友,家乡已成畏途。在被“组织”榨干以后,这些人像药渣一样丢弃在这个伤心之城“刨食”。刘生财参加传销前,有个老乡劝他,他不听,现在他把他称为恩人。两人每次见面都要喝酒,以浇心中块垒。
街头信息栏里的广告刷了一层又一层,刘生财知道这意味着“组织”又增添新鲜血液了,而自己就像被掩盖(在)里面的广告纸一样,没用了但仍被粘连其中。偶尔碰到一个老乡来买橘子,刘生财才会从怅然若失的状态中回过神,表情戏谑地问道:你加入组织没。
无人理会,就像他是在另外的世界里自我调侃。
作者雷磊,真故主编
本文原载《南方周末》